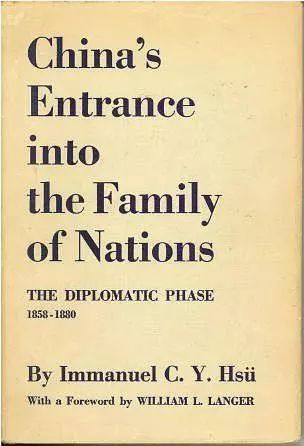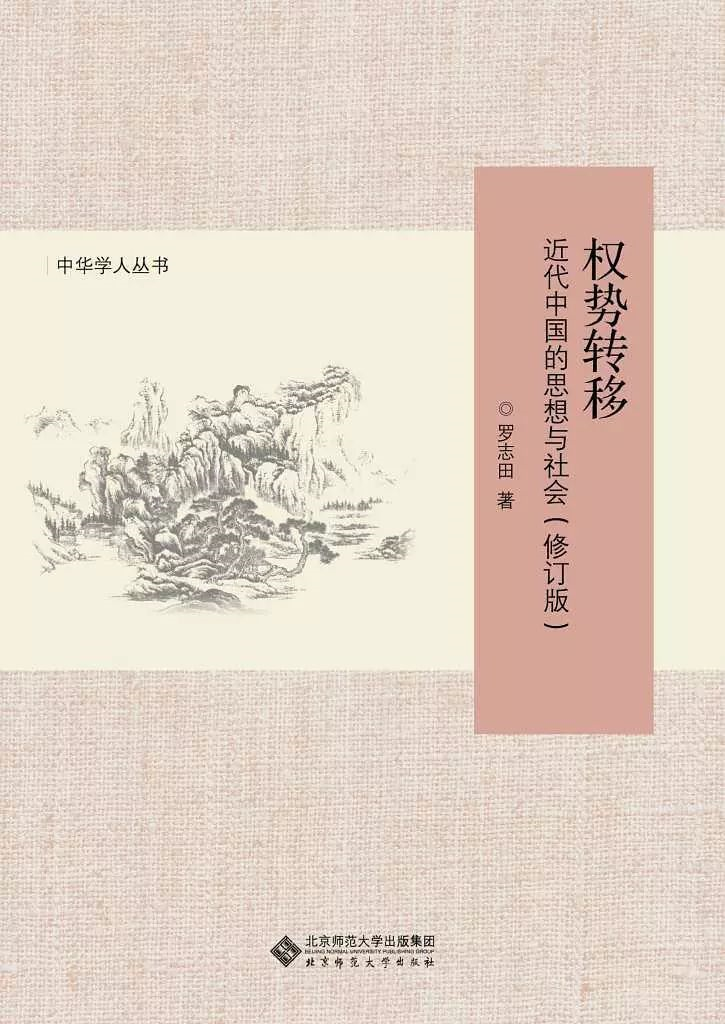國際關系中的政治,其本質特點是沖突與合作。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以來,科技進步、新航路開辟、國家權力擴張,以及開拓殖民地市場等因素,使得大英帝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強國與崛起中的第三世界國家,產生了一套全球化的新秩序。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秩序與國際關系,必須建立在主權國家相互作用的基礎上。 帝制時代的中國,沒有現代主權國家的領土疆界概念,其政府亦不具備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鴉片戰爭的爆發,意味著這個東方帝國在西方列強的炮火之下,必須學會如何與洋人打交道。誤解、隔膜與屈服自不待言。在主流史學的敘述中,一部近代史,便是一部帝制中國如何擺脫西方列強殖民和壓迫的歷史。這一“受害者”敘述,容易導致對那些身處時局的當事人,在外交斡旋中因應傳統中國與現代西方的巨大差異時的歷史細節有所忽略。 歷史學家徐中約教授的《中國進入國際大家庭:1858-1880年間的外交》,運用中、英、法、日等多種語言的文獻資料,通過考察從1858年英方如何在《天津條約》中獲得設立公使館的權力,到1880年中國在西方國家相繼設立公使館的過程,探討建立在主權國家間平等交往基礎上的近代歐美國際法體系,是如何拓展到東亞、取代東亞舊有國際秩序,這也是中國從古老的天朝上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艱難蛻變的過程。 《中國進入國際大家庭:1858-1880年間的外交》
作者:(美)徐中約
譯者:屈文生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18年6月
叩開帝國大門的陌生人 第一次鴉片戰爭,是西方列強叩開中國國門的初次嘗試。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后,西方人在中國境內展開沿海貿易、征收厘金等具體問題被提上議程。在華設立常駐公使,成為西方列強的目標。 然而,此時西方國家的立場并非鐵板一塊。英國并非要同中國建立對等的外交關系,而是希望拓展有利于商業貿易的便利制度;法蘭西帝國在華缺少商業利益,拿破侖三世希望向中國傳播天主教以獲得榮耀;作為英、法兩國的潛在盟友,美國處于隔岸觀火狀態;而俄羅斯政府則認為,英、法此舉將危及自身在遠東地區的利益。列強間的內部差異,為清政府的因應舉措增添了一份撲朔迷離。 這一時期,處理夷務的兩個主要官員是欽差大臣耆英和桂良。耆英有豐富的處理夷務經驗,持調和立場,希望憑借私人友誼和恩惠感化“蠻夷”。然而,與他談判的額爾金使團毫不領情,使得耆英在談判桌上窘迫不堪,“以淚應對”。

額爾金(詹姆斯·布魯斯),英國駐中國的全權代表,火燒圓明園主要罪魁。
咸豐皇帝對耆英失望至極,令耆英自盡以謝天下。在徐中約看來,耆英的悲劇結局,意味著中國與西方在黑暗中相互摸索的第一次失敗——英方原本要在武力戰爭之后尋找和平契機,而耆英本就帶著和平的目的而來。然而,傲慢的額爾金使團,不僅誤判了耆英的立場,也增加了中國與西方列強談判的波折。 中國欽差大臣與西方使節的矛盾,在于秉持“天朝上國”觀念的清政府,認為不應同被他們視為蠻夷的西人建立往來關系。而西方使節則希望通過允許公使常駐北京的國際慣例,與清政府直接打交道。為此,他們不惜以武力相逼。在這一點上,無論是額爾金和他的助手李泰國,還是美國公使列威廉或法國公使葛羅男爵,都沒有本質上的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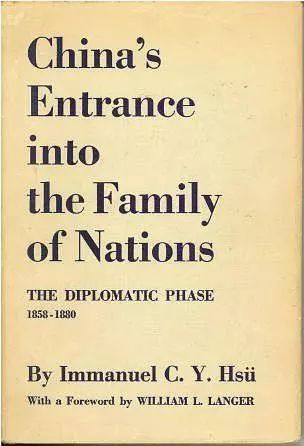
英文版《中國進入國際大家庭:1858-1880年間的外交》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封面,
版本哈佛大學出版社 1960年12月。
妥協與激進的折沖 自鴉片戰爭以降,伴隨西方列強的入侵,大清王朝在官方與民間都孕育出專門負責夷務的買辦與洋務派官員。然而,清廷內部的監察御史和翰林,將自己視作抵御外來侵略者的忠誠衛士,對洋務派效仿夷人的做法激烈抨擊。在徐中約看來,文人士大夫旨在極力維護既有的社會道德與政治秩序。他們無法獲得一手的夷務機密,無從知曉時局的嚴重程度和船堅炮利的強大威力,對制定決策不承擔實際責任,更容易憑借犀利的措辭和冠冕堂皇的話影響圣上。他們提出的御敵之策荒誕幼稚,幾近笑談。 事實上,晚清時期的滿族并非比漢族更傾向于求和,滿族和漢族都是排外的,但是由于滿族掌權者對時局嚴重性有更為清晰的判斷,對朝廷安危的強烈關切,使他們在時局面前的態度更為靈活。他們愿意為了長遠的未來作出讓步。而漢族官吏在朝廷內部多出任文官,他們首要關心的并非朝廷安危,而是維系漢族的傳統和生活方式。 《天津條約》訂立后,盡管中方在這一條約中加入頗多限制條款,但已經無法阻止西方公使在帝國首都居住。作為處理夷務的官方機構,總理衙門應運成立。鴉片戰爭前期,外國人被隔離在廣州。《南京條約》簽訂后,五口通商口岸開埠。清廷加封兩廣總督欽差大臣頭銜辦理五口通商事務。在《天津條約》之后,欽差大臣職務轉移至上海。1861年,西方國家相繼在北京設立公使館,總理衙門應運而生。伴隨這一從珠三角到長三角再到帝都的空間轉移,帝制中國被一步步拖入現代民族國家的洪流之中。

1858年6月26日,在英方“非特無可商量,即一字也不容改”的要求下,中英雙方在天津海光寺內簽署了《天津條約》。這幅刊載于《倫敦新聞畫報》的版畫,是畫師對簽字場景的記錄,左坐者為中方代表桂良,中坐者為額爾金。
朝貢體系崩解與使館制度確立 帝制時代的朝貢體系,是基于儒家禮制思想的產物。奉行皇族家法的清廷,秉持“敬天法祖”的孝道,一心維系祖先創下的基業和定制。在這一制度桎梏下,只有強勢、果敢的皇帝才敢于破除制度窠臼。而咸豐皇帝是一位優柔寡斷者,他傾向于守住既有政治社會秩序。在萬馬齊喑的時代背景下,御史和翰林這一帝制時代最具發聲能力的精英群體,將他們的排外主義發展到極致。在他們看來,只有通過重申儒家道德秩序,才能將夷人驅逐出去。遺憾的是,在船堅炮利的物質文明面前,提倡儒家道德秩序猶如螳臂當車般荒唐而又悲壯。 外國在北京設立公使館,意味著西方國際法在東方的擴張和勝利。盡管,美國歷史學者芮瑪麗提出著名的“同治中興”的說法,但在作者看來,同治時期的外交政策本質上是防御性的,它在帶來良好結果的同時,缺乏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進取精神。 所幸的是,此后數十年,清廷統治者逐漸意識到,條約在使中國為和平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也是約束外國人的必要手段。清廷開始運用國際法規則,向外國派駐外交公使。郭嵩燾、沈葆楨、薛福成等一批朝臣走出國門,增進了對西方列強的了解。至1880年,清廷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和日本設立了公使館。在開展外交關系時,清廷的外交官開始援引國際法,爭取國家權益。這意味著中國已經被帶入世界民族國家的潮流之中,作為天朝上國的時代行將結束。 清末的外交日益影響內政,與“蠻夷”的屈辱往來,也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社會思潮和時人心態。對歷史進程而言,這種影響更為久遠。羅志田曾在《權勢轉移》一書中指出,近代以來,來華傳教士群體,對倚仗船堅炮利的西方列強代理人在華強取豪奪的行徑漸生不滿。這是以拯救和精神解脫為目標的宗教理念,與以搜刮和現實利益為宗旨的世俗欲望之間的沖突。然而,在此岸和彼岸混沌不分的帝制中國官民眼中,他們并無不同,都是非我族類的化外之人。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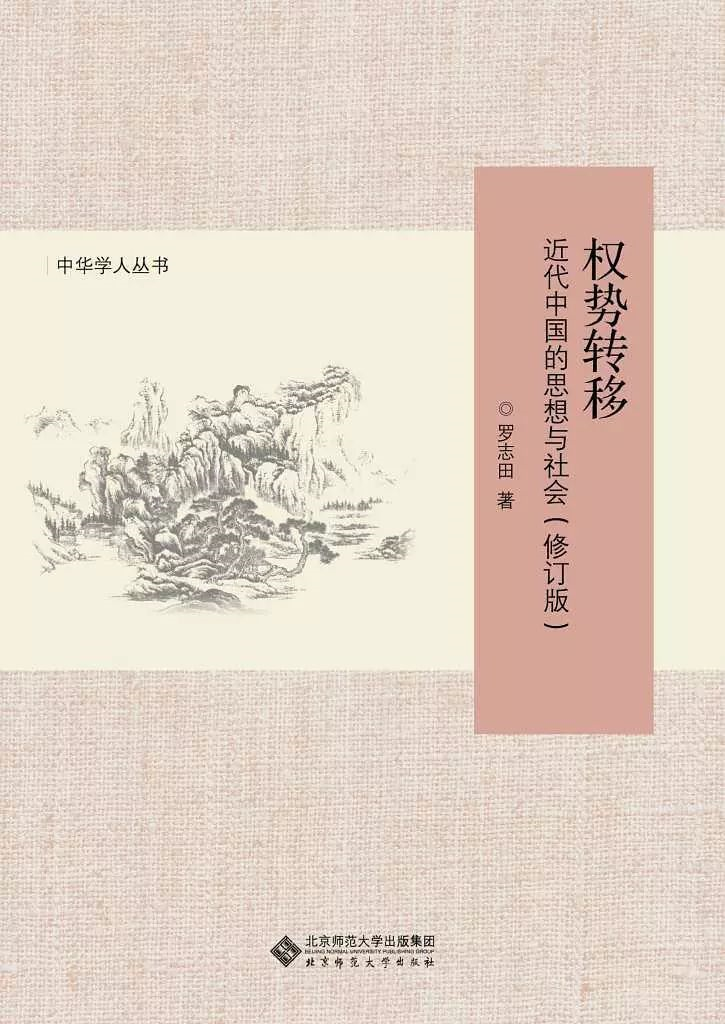
《權勢轉移》
作者: 羅志田
版本: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4年1月
作者通過探討“近代大變局中傳統的中斷與傳承,中西文化競爭與民族主義的特異,思想衍化與社會變遷的互動等各層面的多元互動,揭示近代中國社會新中有舊、舊中有新的豐富特性”。
從19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在洋務派的主導下,帝制中國的政治精英,緩慢開啟了與國際社會接軌的步伐。然而,從《馬關條約》至庚子賠款,秉持儒家道德理想的“清流”——文人士大夫官僚把持了廟堂與民間的話語權,導致了一段激亢、短暫的極端排外的歷史回潮。 民族國家是啟蒙運動與近代工業革命以來的產物,其政治正當性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緣于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對天賦人權的捍衛。誠如作者所言,晚清中國以具有現代主權的民族國家的身份加入國際社會,只是時間早晚問題。然而,民族國家作為具有清晰領土邊界與主權的政治機器,如何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實現主要民族與其他少數邊緣族群的多元共處,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議題。 帝制中國所特有的包容與多元化族群共處等特點,開始為民族國家的批判者所注意。在書結尾,作者畫龍點睛般地指出,中國因迫不得已而加入國際社會,這意味著天朝上國的觀念和價值體系并非蕩然無存。晚近以來,隨著國家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在國際規則的制定中也有了更多的話語權,這個艱難的過程,中國走了一個半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