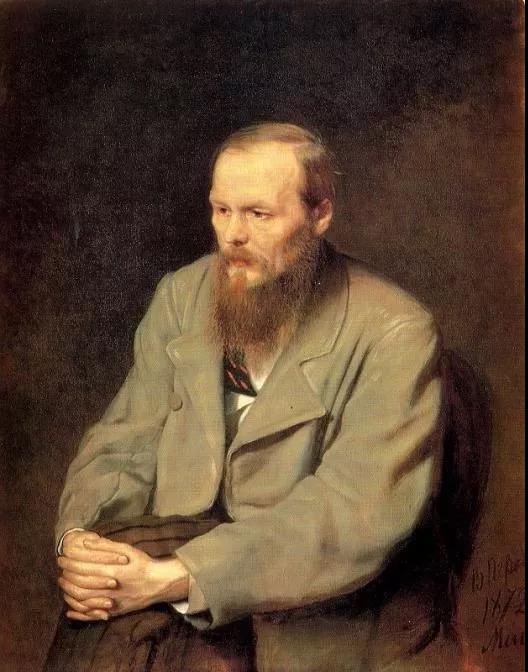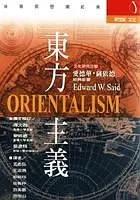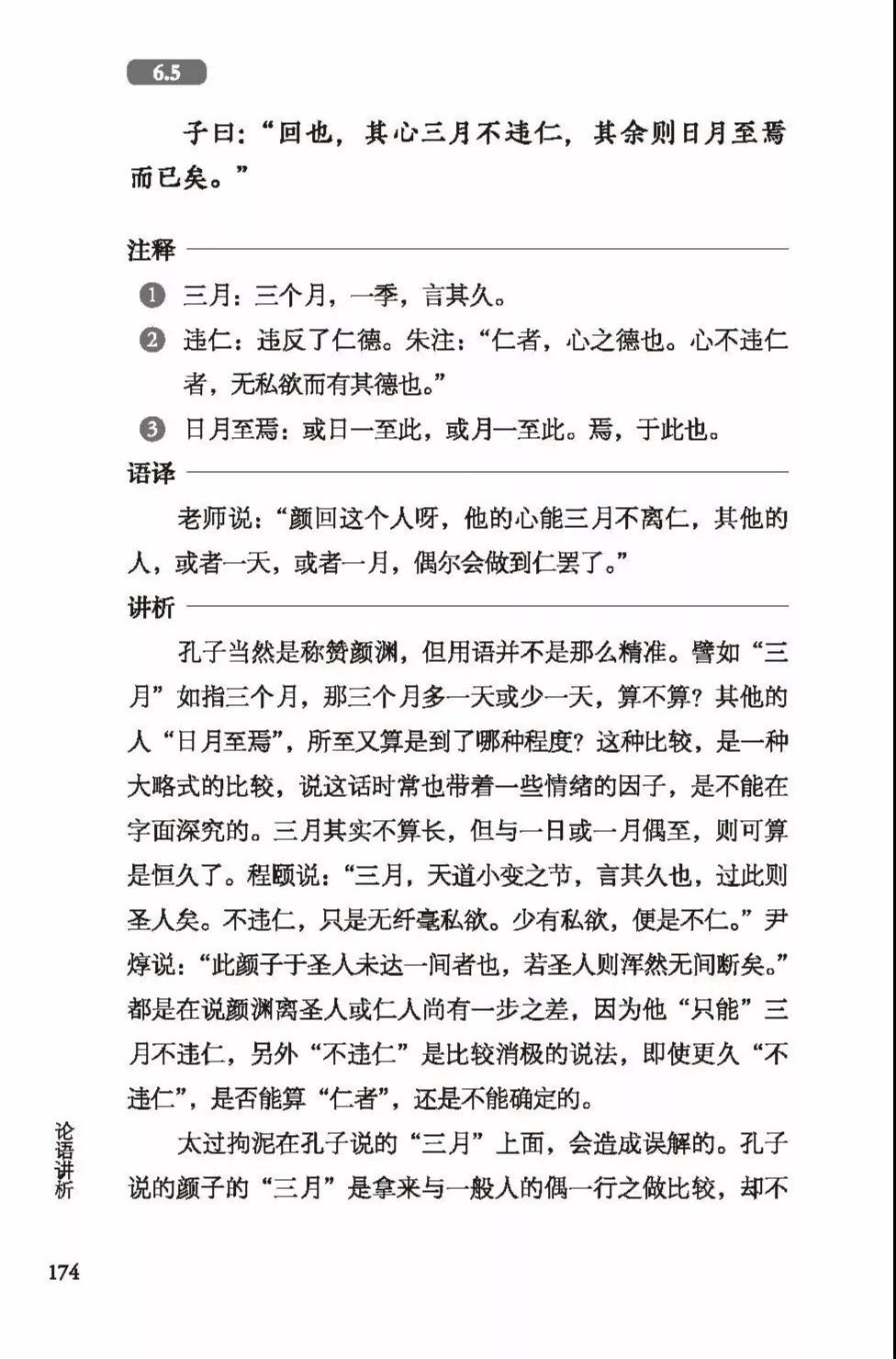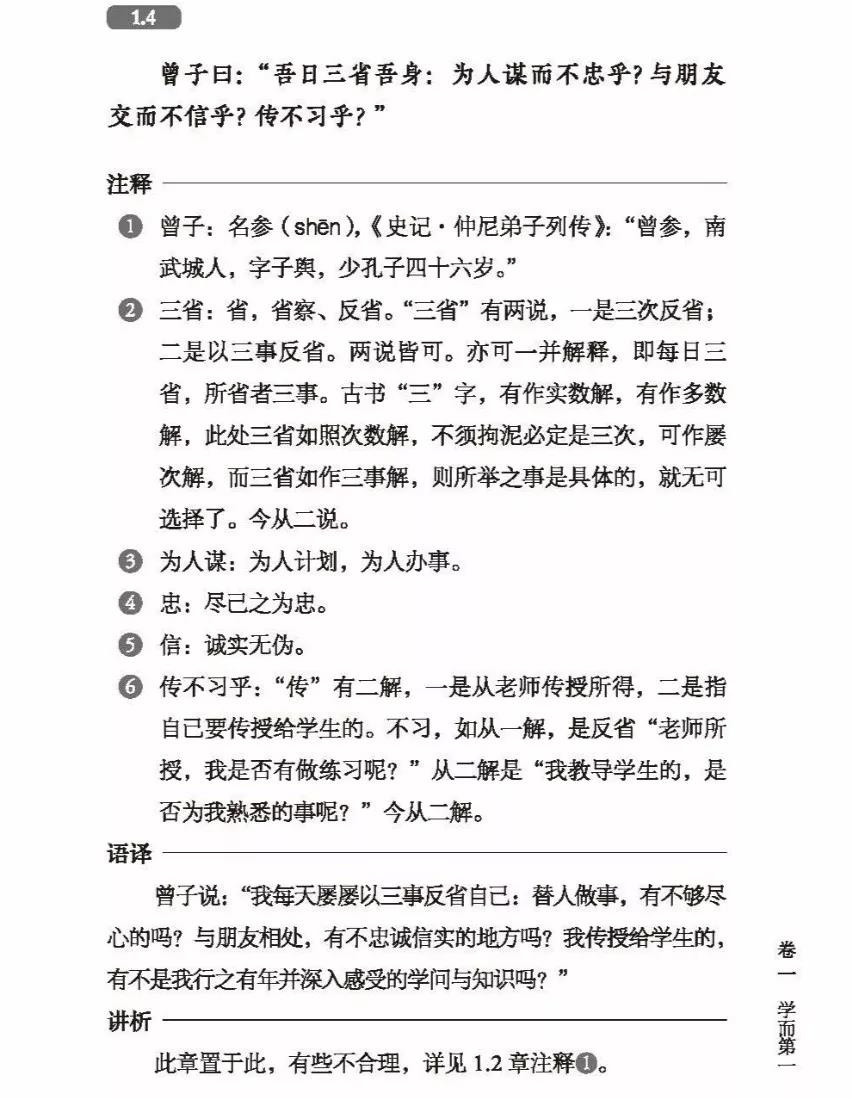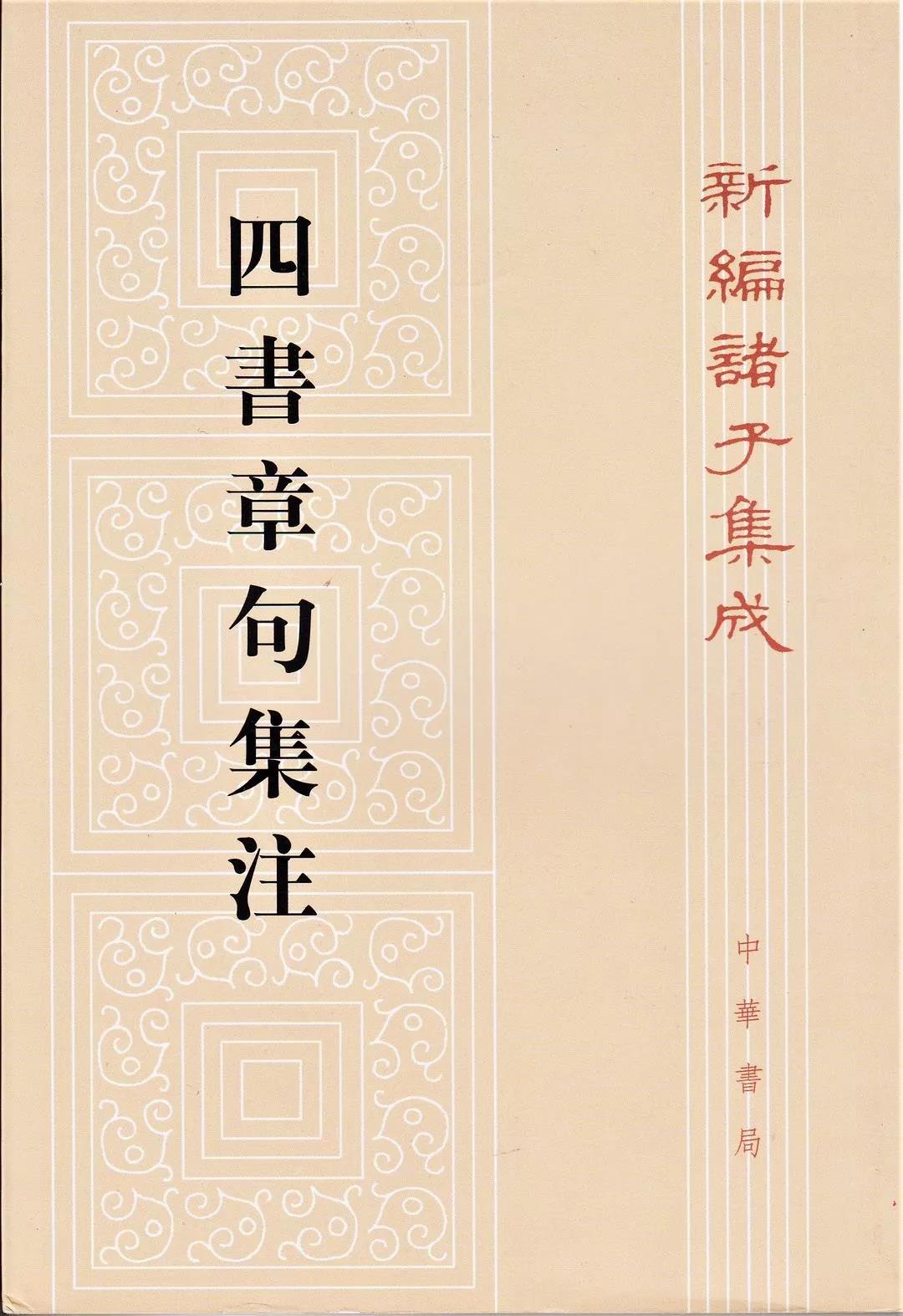周志文,臺灣大學文學博士,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現已退休。學術著作有《晚明學術與知識分子論叢》《汲泉室論學集》《陽明學十講》等,另有散文隨筆《同學少年》《時光倒影》《家族合照》等。
《論語》大約是中國最重要的書,其重要可與西方的《圣經》相較,這是公認的事實。然而我讀《論語》很晚,我上小學時,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語文課本上全是“的了嗎呢”的白話文,一篇文言文都沒有。大約到初一,我才接觸到一點有關《論語》的訊息,好像在國文課第一冊的第四課吧,選了篇《孔子與弟子言志》,便是《論語·公冶長》里“盍各言爾志”那章。教我們課的老師口才一般,沒說出什么令我們折服的道理來,而我們鄉下小孩儲備的知識不夠,其實也沒“折服”的本領,也就含糊而過,未作深思。我中學之前的語文教育,不論中外,那些驚人的文化、文學的精華,我們幾乎一項都沒有碰到過,現在回想,那真是個荒涼的時代! 我們讀高中時,國文課除了課本之外,還有一種書名叫《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必須上的,六個學期六本,內容全是從“四書”選出,其中《論語》的部分最重,篇幅占了全部六冊的三冊,也就是教材的一半,這是我真正接觸到《論語》的起始。但那時青春的烈火始熾,有許多“外騖”要競馳,我的外騖是閱讀令我目眩神迷的西方文學巨作,由英、法的小說開始,終于蘇俄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高爾基,一本一本的,閱讀不盡,眼前不斷翻轉著異國迷人的風景,我生活艱困,有時三餐不繼,弄得骨瘦如柴,身上的一點維持生存的養分,被閱讀帶來的那些昊天的幻想燃燒殆盡,我日復一日捧著那些書本,幾乎過著不見天日的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除了翻譯小說之外,我也一度沉迷胡適,那段時間正是自己的叛逆期,我讀完他四大部的《胡適文存》,深深被他反傳統的理由所吸引。臺灣在中國的邊陲,當時我住的地方,更是臺灣偏僻的一角,而我腦中縈回的,卻是包括廣大的領域與綿長的歷史的中國。但我腦中的那個中國,是個被吸鴉片的男人、裹小腳的女人所充滿,又是個被吃人的禮教所嚴控的扭曲社會,中國沒人身的自由,更缺乏人性的尊嚴,中國的道德虛假、歷史充滿了迷信,而我四周的現實世界雖然狹小,卻也歷歷在目的證實了其中的一部分……那時候我讀《論語》的條件還沒形成。我對中國抱著輕視的態度,不論當代或古代,在這情況下,是不可能展開我傳統文化的壯闊旅程的。 《論語講析》書影
我很早就對上古歷史有興趣,我青年時讀到中國古史,里面說最早的帝王都不是正常出生的,《史記》記殷以契為始祖,其母簡狄行浴之間,見玄鳥墮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周的始祖后稷,其母為姜原,姜原一次在野外,見到一巨人足跡,也許為了好玩,將自己的腳踐在足跡上,《史記》寫道:“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其后秦的先祖母親又重復殷契的后塵,吞了玄鳥所生之卵,這些記錄充滿明顯錯誤與迷信,都為我心中負面的情緒做了精準的注腳。幸好碰到一個機會,讓我有反省的可能,正遇上舉世歡騰的圣誕節,連貧窮的臺灣也跟著瘋。圣誕節是慶祝基督教教主耶穌基督生日的重大節日,所有基督徒都堅信他們的主是上帝之子,耶穌基督的母親是未經一般人受孕的方式生下耶穌的,據《圣經》記載,是上帝借“圣靈”(Holy Spirit)讓耶穌的母親懷孕。我突然想到,我們如“尊重”西方人說他們的教主非人所生,為什么不能“容忍”中國人說我們帝王的母親是踐巨人之跡或吞玄鳥之卵而生的呢?古史往往是跟神話雜糅在一起的,這是一個由神權過渡到君權的時代必然產物呀。西方人用“三位一體”(Trinitas)的理論,來解釋他們神人同棲的方式,為何中國人用了同樣方式就不可以?書逐漸讀多了,懷疑還是不變,但懷疑的主軸有點不同了。后來我漸漸知道,談起吃人的禮教,五四人憧憬的西方,也是有“禮教”存在的,西方的禮教不像中國,是由縉紳之士為主導,而是由更具權柄的教會來帶頭,不要說你不信教得受懲罰,解釋教義與權威有沖突,就得火刑侍候,以至死人無算,而且極其殘忍,就是科學家的主張有點與《圣經》所載不同,也得備受制裁,天文家哥白尼與數學家伽利略都是有名的受害者,證明西方禮教“吃人”的程度,比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還有西方也有極不公平的司法,也有極愚昧的歷史詮釋。這些事都很不光彩,要說也絕對是說不完的。歷史有偶爾蹦出的智慧火花,也有許多愚昧與不幸,不論東西世界都一樣。我讀高中的時候,對《論語·陽貨》篇的一章十分反感,便是孔子說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那章,當時平權的想法甚盛,心中以為,孔子怎能把女子與小人同視,男女不該天生是平等的嗎?后來讀了《圣經》,也讀了一些通俗的佛教讀物,原來在偉大的宗教中,男跟女是完全不平等的,西方的民主觀念,也是到了二十世紀之后才比較“落實”到女性同胞身上,譬如美國,到一九二零年之后,女子才有政治上的投票權。總之,男女是“該”平等的,但這平等不是“天生”就在那兒,是靠人類憑理性與努力,不斷爭取得來的,正如薩義德在《東方主義》(Edward W. Said,1935-2003:Orientalism)一書中所說:“現代化、啟蒙與民主之類的,絕不會像在客廳找復活節彩蛋一樣,是那么簡單明了、普遍接納的觀念。”圣人是人,也受制于時代,不是凡事都能超越的,譬如孔孟時代人不知道有現代的民主政治,也不知道現代人有手機可用、有飛機可乘一樣。體悟到這些,才能用比較寬容的態度看中國與世界的歷史。《東方主義》是一本有關歐美如何看待中東,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兩百年學術傳統的權力與想像的研究。薩依德以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論以及富柯的知識權力論為其論述的基礎。將東方主義者在全球性的網絡中,所建構的西方殖民勢力對東方世界權力的支配,知識再生產之霸權架構,殖民與被殖民者,西方與東方之不對等權力關係以及煮奴式的霸權體系一一展演於前。五四時代的人還喜歡作不當的切割,譬如說文言是落伍的,白話是進步的,更因為文言難懂,白話易懂,便說文言是“死文學”,白話是“活文學”,又說中國的一切落伍、外國的一切進步,東方的一切有罪、西方的一切可原諒。其實這樣“一刀切”是錯誤的。就先以文言白話之爭來看吧,我們拿《論語》中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中的某些句子作比較,哪個更易懂、哪個更難懂呢?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還有許多古詩古文,恐怕一直“活”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靈之中,到現在依舊靈動又生活化,并不如他們說是“死文學”的吧。這種憬悟是逐漸形成,而非成于一日,厘清迷霧,用了我不少時間,但整體而言,是值得的。回頭來談《論語》。我讀大學后,開始比較能用心平氣和的方式看這本書了,不只是《論語》,也包括其他中西的書籍,慢慢地讓我看出了一點端倪。我逐漸覺察出《論語》是一本非常親和的書,里面所記孔子與弟子的對話,都是平常話,所記的孔子跟弟子的生活,也是很平常的生活,所以說《論語》是本很親和的書,但里面含有不少大道理。原來平常的語言、平常的生活是可以寓有大道理的。《論語》可以匆匆讀,也可慢慢讀,不論怎么讀,都可以開啟智慧,也可開啟心胸。清人以義理、考據、辭章來分析文章,細讀《論語》,可以得到各方的滿足,所以我主張要慢慢讀這本書的。讀者會發現,我在這本《論語講析》書上用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作為全書的題詞,這一方面是紀念我與《論語》的初次相遇,一方面是這三句話包括了太多的含義,值得我們反復思考。我就以此章為例,以義理、考據、辭章的方式做一說明吧。此章記的是孔子跟兩個弟子顏回與仲由聊天,聊到各人志愿的事。首句是“顏淵季路侍”,“侍”是晚輩陪長輩的禮貌用詞,顏淵名顏回,字子淵,此處不直接叫他顏回而叫他顏淵,同樣仲由字子路,此處不直接叫他仲由,而叫他季路或子路,是為什么呢?是這樣的,假如此章為顏回或仲由所記,當然得自稱是“回”或“由”了,但此章是由顏回或仲由的弟子或再傳弟子所記,依禮,同輩或晚輩不得直呼其名的,所以文中都以字稱之了,但孔子如叫他們,就直接叫“回”或“由”了,《論語》中有很多這樣的例子。由這樣小的地方,都看得出古人有條不紊,絲絲入扣,可見孔門是如何講究“禮”的。《論語講析》內文當然此章的主旨不在言禮,而是知道講起禮來,禮可以無處不在的。此章所談是人生的方向,《毛詩序》言:“詩者,志之所至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人生的方向豈不是最該關懷的嗎?子路與顏淵,一個大氣慷慨,一個狷介清守,都相當與眾不同,等到子路問老師的志向,孔子不急不緩地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平行又平穩的三句話,看起來聽起來一點也不覺得有什么特別,但要細看細思,就知道其中的含義多么豐富了。就像聽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的第三樂章,標題寫的是《如歌的慢板》(Adagio molto e cantabile),你千萬不能以為只是如字面的注記而將其輕輕帶過,沒有這如歌般的慢板樂章,最后一樂章的主題《快樂頌》無法展開,其實“善聽”的人在這緩緩的樂音中,已經聽到不久就要到來的大消息了。貝多芬用了德國大詩人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終極關懷的詩做交響曲的結尾合唱,詩的主題是“世人都將成為兄弟”(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其實席勒的這句詩像極了《論語》里面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也跟《禮記·禮運》篇所記的“大同”理想極為近似,不同的是《論語》說得更具體,而《禮記》說得更全面,還有最大的差別是,席勒是十八到十九世紀的人,而《論語》或《禮記》都是兩千多年前的中國人所寫的書了。其實孔子的這三句話,平穩無波的跟貝多芬的第三樂章一樣,而內容則如驚濤駭浪的包含了第四樂章的所有,我們試著細推演一下:“老者安之”是指要使老年的人過安定的生活,老人曾對我們的社會有所貢獻,他理該在老年時過承平的好日子。“朋友信之”指與我平行的人都能以誠信相待,朋友都能誠信相待,世上便無虛假的事。“少者懷之”指少年的人要懂得懷恩,這一方是要少年人謙遜,要懂得飲水思源,這是少年人的修養,另一方面,是要讓少年人有恩可懷,這便是“大人”的責任了。三句話沒一句唱高調,都是非常誠懇踏實的話。空間上,孔子關心世上的老、少還擴及一般人,幾乎包含了我們社會的所有。老者、朋友與少者,又象征了時間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從時間上看,孔子的關懷更是久遠,這三句話與《禮記》說的“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的說法是完全一致的,但卻更有力,因為還包括了時間的因素。孔子關心所有的“人”,也關心人的所有的各項層面,卻從不談怪力亂神的事,這是中國很早就走入“人文”社會的原因。西方自十四世紀文藝復興之后,史家常以“人文”程度為標準來檢視人類文明的進步與否,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注意,在《論語》寫成五六百年之后,《圣經·新約》還有耶穌以五餅二魚來喂飽五千男眾,也有耶穌在水上行走的記錄,相形之下,孔子一無神跡可顯,他不是神,其實也做不到,但他卻做出最高遠的人文關懷,我們可以說,人文精神是《論語》最珍貴之處,也是傳統中華文化最珍貴之處。 《論語講析》內文
除了人文關懷之外,《論語》還記錄了孔子的寬容與博大,還有優美。我常覺得,孔子的道德是一種美學,道德在孔子而言不只是規范,而是優美的生活。子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語氣有點無奈,有點哀傷,但臨流感嘆,不是也帶著美的意含嗎?孔子又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指不義的富貴與我無干,算起來也很平常,區別是一般人說這話時往往陳義過高,又嚴詞逼人,而孔子說這話時,卻把情緒放緩了,以天空的浮云相況,是多么高明又優美的境界? 這優美其實還包含著寬容,意思是我雖絕對不要這不義的富貴,但世上有些人竟要了,也許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在的,假如是生存所寄,我也無須對之指責鄙薄過甚,這是孔子謙和寬大之處。還有,儒家十分注意“禮”這個字,孔子答顏淵問雖說過:“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但在孔子的說法里,禮并不是那樣的硬邦邦的,禮是一種秩序,人雖向往自由,但人對秩序的要求,也是天生自成的,所以禮不見得與人性沖突,人既生活于社會,自須有些秩序的節制,儒家強調的禮是與人的至高感情結合的,是自覺而非他律的,不合至高感情的禮,才可能“吃人”,有情有禮的結果,人才可以在世上“立身”,故曰:“不學禮,無以立。”
《論語》記的是孔子與弟子的言行,不是孔子所自記,應該是孔門弟子或再傳弟子所記,但整體上言,可信的居多,不可信的很少,不可盡信的如《季氏》篇的“邦君之妻”與《微子》篇的“周有八士”章,應是與《論語》無關的雜記,由于都在兩篇的最后,也許是后人在抄寫時無意抄入的。 但如置于一篇的中間,那些表面無關的章節,可能是有意放進的,而非誤入。譬如《微子》篇中有“大師摰適齊”一章,寫的是幾個宮廷樂師散落各方的情形,朱注引張載言:“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后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張載認為是寫孔子在時的魯國衰敗,其實此章與孔子或孔門弟子一無關系,因為文中的“亞飯”“三飯”“四飯”都不是周朝更不是魯國的制度,所以從考據學上言,此章有很多問題的。
《論語》為何存有此章呢?我以為《論語》的編者有更高的目的,或是想要讓《論語》這本書具有文學或美學的性格,此章主要要顯示《論語》編者對孔子所處的時代有強烈的淪喪感或寥落感。孔子本人也有意志消沉的時候,當然他終于克服了,但他畢竟對他的時代是有淪喪感的,《子罕》篇記孔子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可見傷心的程度。
我總覺得最高貴的人與最高貴的文學,都有這種情愫在其中的,杜甫的《秋興》、劉禹錫的《烏衣巷》與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的《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都有強烈的淪喪感,這種淪喪感的目的不在讓我們墮落,而是讓我們體會人生在世最深沉的一面,讓我們知道,就算是圣人也會有遭時不順、意志蕭條的時候,王陽明說過:“圣人居此,更有何為?”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1866-1944)在他的《約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的前言上寫道:“戰士啊,當你知道世上受苦的不止你一個時,你定會減少痛苦,而你的希望也會在絕望中再生吧!”我想,要的就是這種體會。
《論語》值得作更多的美學探索,例子是舉不完的,我在書中試圖點出,讀者可細看全書。我后來讀《論語》,覺得比讀其他的書,內心更感到踏實又飽滿,而又洋溢著美感,這是我無論旅行或居家,身邊總會帶著的一本書。我常讀的是《論語》的白文,不太看別人的注解,當然反復的閱讀,也必會接觸到歷來的各種注本,有時涌出一些自己的意見,與他人的說法有所不同,心想何不記下來呢,有這念頭,是自己剛開始在中學執教鞭的時候,真想寫,大約有三四十年之久了。因為積累久了,真要寫時,心中有太多言語,下筆往往不能自休,也偶爾因過于強大的感懷或聯想而停下筆來,便這樣斷斷續續的花了半年的工夫,每天伏案幾乎十個小時,寫時累人,不寫時更傷神,終于完成了這本《論語講析》。兩千年來留下的資料實在太多了,但因為目的在為普通讀者講析,必須要言不煩,我還是用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為底本,因為這本最為通行,解說也較為允當,其間也參酌了古人時賢的一些有關著作。我讀《論語》時有自己的看法與想法,太屬于個人的意見,或者有些動了情緒的,我想放在之后要寫的《讀論語札記》中吧,也就不放在此書中了。本書集儒家經典中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一書,注重義理的解釋與發揮,對文字訓詁也很注意,字斟句酌。此次整理以清嘉慶年間吳縣吳氏父子校刻本為底本,用清康熙內府仿刻的宋淳祐二年大字本校勘。但一些不得不明說,譬如歷來解釋錯了,還是得指出的。像《學而》篇子夏曰:“賢賢易色”一章,朱子認為賢賢易色是指“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把色字當成好色的意思解了,問題是當一人見賢者在座,是“很難”起好色之心的,所以朱子的說法是有問題的,但不幸是后儒多從朱說,當代的錢穆先生也解作:“謂以尊賢心改好色心。”明顯是采用了朱說,李澤厚先生雖有修正,注中引《論語正義》“猶言好德如好色也”之說而改成“愛好德行如同愛好容貌”,但還是不很清楚。我認為此處的“賢賢易色”是見到賢人在前,要收起平常輕漫之容色而肅然起敬,這例子在不難找到,《為政》篇有:“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其中的“色難”的色字即指人的容貌顏色而言。還有歷來的注家都太在意儒家的純粹性,一涉及書中載有道家或其他派別的思想,就懷疑《論語》記載有誤,譬如《先進》篇有名的“浴沂歸詠”一章,后世就有人認為孔子不該稱許有道家思想的曾晳,而忽略了走儒家“正路”的子路、冉有、公西華等人,便有了像崔述一般的論斷說:“此章乃學老莊者之所偽托而后儒誤采之者。”其實道家很多思想不見得與儒家沖突,其中所涉的精神層面,也是高度相同的,孔子一生,也有“道不行,乘柫浮于海”的喟嘆,在“鳳鳥”久盼不至的年代,圣人也偶會興起蕭瑟之感。還有此章寫的是孔子與弟子游賞風景,正沐浴在怡然的春風之中,心情自不免隨之放松,便暫時放下修身、治國的心事,孔子贊嘆曾晳“浴沂歸詠”,認為他的說法更優美而自然,就并非不可思議了。在孔子或孔子稍后的時代,儒家與道家思想是可以兼容的,這一方面可從《論語》中找到材料,一方面也可由《莊子》書中找到材料,譬如“莊學”中最重要的理論“心齋”、“坐忘”,都是舉孔子與顏淵為例的,這些都看得出來早期儒、道之間彼此兼容的性格。這類的觀點,我在書中都試圖點明出來了。我想在這一部分,我的《論語講析》也許有點化解壁壘的作用。像這樣的例子很多,譬如禮與美學的關系,《論語》后半部偶出現孔門弟子沖突的問題,我常有與傳統不很相同的意見,這些意見,我在書中都點了出來。《論語》不是放在博物館的陳列品,它是活著的,《論語》既活著,就應讓它流轉不息,該讓它容許一些新的解釋在其中,這是我的想法。但傳統的注本也是極重要的,絕不可拋棄,為了求真,解釋可以修正,不可以全盤否定,因為是它使經典的生命延續下來,沒傳統的注本,《論語》早就消失了。 《論語講析》書影
寫這樣一本書,有些是我個人的因素,還有外在的原因,我總是想到我們當今中國人的處境。有什么當今中國人的處境呢?這就比較復雜了。與其他歷史悠久民族相較,當今中國人所面對的問題有點特殊,像猶太與阿拉伯民族,到現在還要面對相當程度的生存壓力,百年前的中國是一樣的,否則沒有梁啟超《愛國歌》“每談黃禍詟且栗,百年噩夢駭西戎”之言了,而目前的中國,可以說已掙脫了那個壓力了。另外如埃及與印度,他們都能夠生存無虞,但在他們之間,缺乏一種強而有力的文化傳統來維系他們的心,大部分的埃及與印度人無法說祖先的語言、用祖先的文字,他們雖然繼承著祖先的血液,卻大多數已與祖先斷了音訊。中國不同,所有認識漢字的中國人,幾乎可以透過書籍相當“直接”地與我們的祖先溝通,我們歷代祖先建構的文化價值,仍不絕如縷地存在于我們生命之中,比起那些種族,中國人的血管不僅流著祖先的血液,神經也如電網般傳遞著古老的信息,直接又快速,而且一刻也未曾停止,整體而言,中國是“有根”的民族。這種現象在世界的文化圈中,是很少見的。對當今中國的憂慮的不是傳統消亡,而是扭曲。扭曲有時是無意,有時是有意。扭曲的禍害,比一點不剩的消亡更甚。完全消亡了傳統的人成了另一種人,也可以簡單地活著,而扭曲的人就成了不斷自毀自殘的人,結局可能就更為可懼了。這是我寫這本書的最大的動機。我辛勤寫作,勉勵我的是這本《論語講析》也許能為有心的中國人找出更多歷史的真相,讓我們重新認識一些既有的傳統,我相信,當我們不再扭曲我們的祖先與我們自己,我們便能更自信而且毫無愧怍地面對當今的世界。有幾個朋友看了本書的部分,說寫的還不錯,認為一些地方恐怕有“超越”古人時賢之處,我說不敢當,我知道是獎掖鼓勵我的意思。我雖對一些歷來的解釋不以為然,有時不得已用了些批判的字眼,但態度是恭謹的,偶有一得之見,是因為我思考得夠久,而這本書又是新作,被我批評的古人時賢,不是沒有機會,或是來不及答辯,對他們而言,也有不公平處。也許再等些時候,有人認為我寫的錯了,我曾自以為是的意見也是千瘡百孔的,也會用同樣方法對我了,我覺得,要是這樣很好,不是說學問是天下的公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