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因斯坦說,有兩種東西是無限的,一是宇宙,一是人類的愚蠢,不過對(duì)前者我沒什么把握。日本歷史學(xué)家堀田江理(Eri Hotta)這本《日本1941:導(dǎo)向深淵的決策》講述的歷史,真是應(yīng)了愛因斯坦這句話,它以起居注般細(xì)致入微的史料,重現(xiàn)了1941年4月到12月這八個(gè)月里日本軍政當(dāng)局發(fā)動(dòng)太平洋戰(zhàn)爭的愚蠢過程,其中不少細(xì)節(jié)足以讓讀者瞠目結(jié)舌。
1868年,日本開啟現(xiàn)代化高速轉(zhuǎn)型的明治維新時(shí)代;1889年,日本頒布帝國憲法,成為亞洲第一個(gè)成文憲法國家。1894年,日清戰(zhàn)爭中打敗清朝,日本一躍而為亞洲強(qiáng)國;1904-1905年,日俄戰(zhàn)爭中殲滅俄國波羅的海艦隊(duì),日本再躍而為世界強(qiáng)國;1914年,日本對(duì)德宣戰(zhàn),搶占了德國在華利益(巴黎和會(huì)上歸還了部分)。國際爭端中屢獲巨大成功,催生了日本濃重的霸權(quán)意識(shí),當(dāng)局仿效歐洲的帝國主義風(fēng)格,就像笑話里的笨裁縫學(xué)徒,連樣衣上的補(bǔ)丁都老老實(shí)實(shí)照抄下來。日本從此開始了全面稱霸亞洲的國家戰(zhàn)略,從日清戰(zhàn)爭中收獲的臺(tái)灣和朝鮮殖民地,早已不能滿足它;然而,侵華以及全面占領(lǐng)中國,甚至向北與蘇聯(lián)為敵,向南覬覦英法荷殖民地、試圖搶奪東南亞資源并控制太平洋重要航道、與法西斯德意結(jié)盟,損害英美等國在遠(yuǎn)東的利益,……這一切都招致了英美的強(qiáng)烈反感。
因?yàn)榍秩A戰(zhàn)爭,美國從1938年開始,就對(duì)日本相繼實(shí)施了各種制裁,包括飛機(jī)零部件的“道義禁運(yùn)”(1938年7月1日)、禁止出口工業(yè)設(shè)備(1939年6月4日)、嚴(yán)控金屬、航空燃油和潤滑油的對(duì)日出口(1940年7月底)、禁止出口鋼鐵和廢鐵(1940年10月16日),尤其在1941年7月28日日本占領(lǐng)法屬印度支那之后,美國立刻凍結(jié)了日本在美國內(nèi)的所有財(cái)產(chǎn),包括實(shí)行石油禁運(yùn),隨后英國和荷蘭加入制裁日本的行列。日本由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資源困境。
入侵中國東北后不到六年,1937年7月7日,日軍全面入侵中國。然而,軍部所謂中國三個(gè)月投降的如意算盤算珠灑地,到1941年下半年,日本陷在這個(gè)巨大的泥坑里已將近四年半。久拖不決的戰(zhàn)事、與德意結(jié)盟,給日本帶來了多重危機(jī):國際形象一落千丈、能源匱乏(“由于石油和煤炭需留作軍用,日本國民不得不依靠木炭生火做飯、取暖;甚至公共汽車也依靠木炭提供動(dòng)力”頁7)、戰(zhàn)略物資的來源岌岌可危(“1940年,日本93%的石油來自美國”頁8)、國民生活日益困苦——《深淵》引用了世情作家永井荷風(fēng)的戰(zhàn)時(shí)日記,“我已經(jīng)有好幾天沒見過任何蔬菜或水果了,豆腐也買不到,大伙都感到很憂慮。”。
正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nèi)背景下,日本如伊索寓言中那只與水牛比拼肚皮而自吹自爆的青蛙,迅速自我膨脹,迅速走向末日。《深淵》從這里進(jìn)入歷史敘事,作者在中文版序言里說:
“與公認(rèn)觀點(diǎn)不同的是,本書認(rèn)為,日本領(lǐng)導(dǎo)人其實(shí)認(rèn)識(shí)到發(fā)動(dòng)這場(chǎng)戰(zhàn)爭將帶來毀滅與自我毀滅的后果(當(dāng)時(shí),日本企劃院估計(jì)美國的工業(yè)產(chǎn)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甚至在發(fā)動(dòng)襲擊前的幾個(gè)月里,日本領(lǐng)導(dǎo)人也本可以避免這一對(duì)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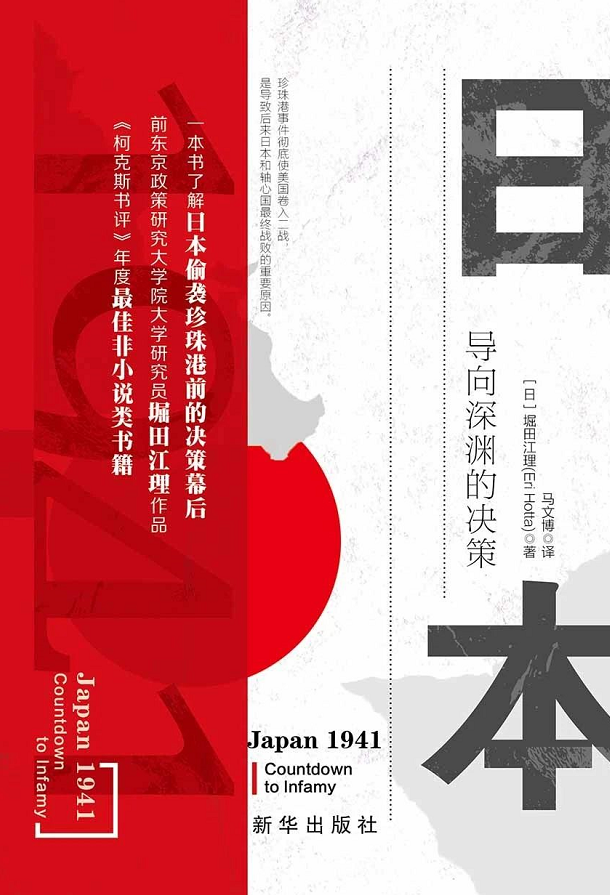
《日本1941》
確實(shí),即使不了解日本發(fā)動(dòng)太平洋戰(zhàn)爭的具體決策過程細(xì)節(jié),一個(gè)普通人只要頭腦正常,都能判斷此時(shí)挑起與美國的戰(zhàn)爭是多么愚蠢,更何況掌握了帝國全面資訊的當(dāng)局者。在1941年10月27日的一次內(nèi)閣會(huì)議上,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報(bào)告了一組數(shù)據(jù):
“1940年,……美國的石油產(chǎn)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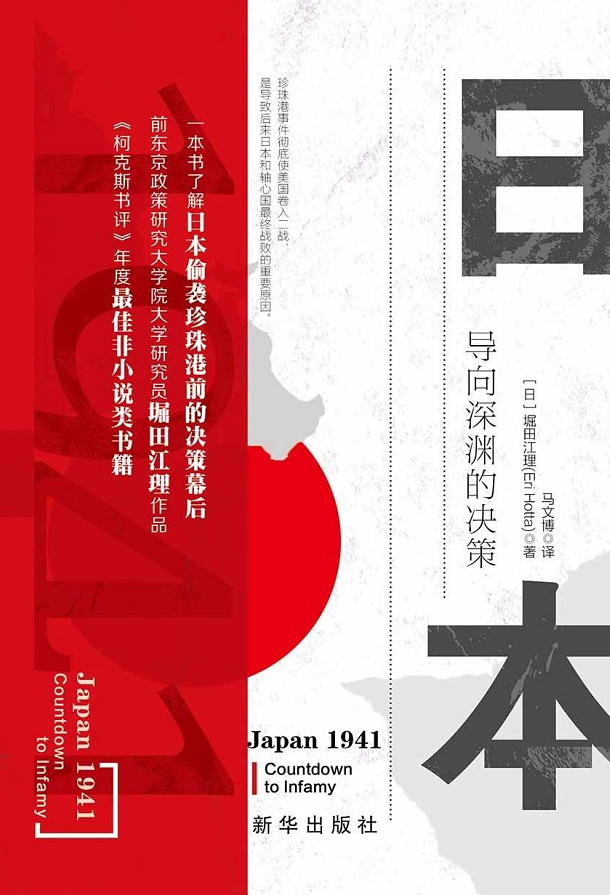 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鐵20倍,銅塊9倍,鋁7倍。再加上其他產(chǎn)品,比如,煤炭、汞、鋅和鉛,美國的平均工業(yè)產(chǎn)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而陸軍的估計(jì)為20倍)。”
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鐵20倍,銅塊9倍,鋁7倍。再加上其他產(chǎn)品,比如,煤炭、汞、鋅和鉛,美國的平均工業(yè)產(chǎn)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而陸軍的估計(jì)為20倍)。”
按理說,看到這樣的數(shù)據(jù)對(duì)比,任何一個(gè)有著基本常識(shí)的政府,都會(huì)打消發(fā)動(dòng)戰(zhàn)爭的念頭,那么日本政府為什么還會(huì)作出愚蠢和錯(cuò)誤的決定?《深淵》要解答的就是這個(gè)問題,也是讀者震感強(qiáng)烈的原因:它展示了人類歷史上其實(shí)十分常見的一種現(xiàn)象,即當(dāng)國家操控在一群既無無理性也無擔(dān)當(dāng)、只會(huì)抱團(tuán)在豪言壯語里虛張聲勢(shì)的軍政官僚手中時(shí),人民將會(huì)罹受什么樣的深災(zāi)巨劫。
《深淵》全書正是圍繞著這一主題組織史料,史料的起訖時(shí)間主要集中于1941年4——12月這八個(gè)月間。在走向毀滅的這八個(gè)月之前,由于軍部尤其是陸軍的長期不斷坐大,文官政府要將日本這首巨艦從命運(yùn)的危險(xiǎn)海域里掉頭已經(jīng)非常困難。
《深淵》涉及的日本軍政要人,包括裕仁天皇、木戶幸一(內(nèi)大臣)、近衛(wèi)文麿(內(nèi)閣總理大臣)、東條英機(jī)(陸軍大臣、內(nèi)閣總理大臣)、松岡洋右(外務(wù)大臣)、豐田貞次郎(外務(wù)大臣)、東鄉(xiāng)茂德(外務(wù)大臣)、及川古志郎(海軍大臣)、永野修身(海軍軍令部總長)、來?xiàng)桑ㄗ詈蟾懊勒勁械耐饨惶厥梗⒁按寮桑ㄈ毡咀詈笠蝗务v美大使)、山本五十六(海軍次長、海軍聯(lián)合艦隊(duì)司令長官)等,作者通過史料,對(duì)這些人物在八個(gè)月間的所言所行描繪出一副日本愚政責(zé)任人的群像。
西園寺公望是曇花一現(xiàn)的大正民主時(shí)代最后一位元老,近衛(wèi)文?雖是他門生,但因偏向德國法西斯而反對(duì)議會(huì)民主,與主張自由民主以及國際道義的西園寺漸行漸遠(yuǎn)。西園寺不僅曾為此“勃然大怒”,甚至不支持近衛(wèi)的第二屆內(nèi)閣。據(jù)歷史學(xué)家伊藤之雄《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導(dǎo)者》考證,早在近衛(wèi)文?第一屆組閣時(shí),西園寺公望即認(rèn)為他性格懦弱,為了獲得支持不惜屈意迎合,組閣后必定會(huì)被軍部牽制,而置國家于險(xiǎn)境,以至于作為元老對(duì)來自皇室的咨詢連形式上的奉答都拒不作出,其失望之心可想而知。事態(tài)發(fā)展果如西園寺判斷,近衛(wèi)文?1937年第一屆內(nèi)閣上臺(tái)后一個(gè)月,就爆發(fā)了“7.7事變”。他的這一屆終止于1939年1月5日的內(nèi)閣總辭,自稱厭倦了作軍方的傀儡。1940年7月22日,近衛(wèi)第二次組閣;二個(gè)月后,簽署了德意日三國同盟協(xié)定;10月12日,成立大政翼贊會(huì),禁止其他政黨,開啟集權(quán)的法西斯體制,即所謂“新體制運(yùn)動(dòng)”,給了日本政黨政治最后一擊;一個(gè)多月后,西園寺去世,近衛(wèi)文?從此更無顧忌。第二屆組閣后,近衛(wèi)內(nèi)閣在日美關(guān)系惡化的道路上加速行進(jìn),1941年7月18日,為了擺脫跋扈而張揚(yáng)的外相松岡洋右,近衛(wèi)內(nèi)閣總辭后重組第三屆內(nèi)閣,其他大臣原封不動(dòng),只將外務(wù)大臣換成豐田貞次郎。
美日關(guān)系走向不可救藥的敵對(duì)狀態(tài),正是發(fā)生在近衛(wèi)文?的第二、三屆內(nèi)閣期間,而近衛(wèi)第一屆內(nèi)閣留下的侵華爛攤子,在平沼騏一郎、阿部信行、米內(nèi)光政三屆內(nèi)閣領(lǐng)導(dǎo)下,也都未能解決。“近衛(wèi)文麿魯莽而極權(quán)的領(lǐng)導(dǎo)方式對(duì)日本的國際地位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害,也讓軍隊(duì)對(duì)政府的影響力達(dá)到頂峰。”雖然,“近衛(wèi)領(lǐng)導(dǎo)下的日本仍在努力從中國戰(zhàn)場(chǎng)脫身”,第二屆內(nèi)閣時(shí),“他希望結(jié)束這場(chǎng)沖突”。這種自相矛盾的狀態(tài),以及由此帶來的中日兩國的災(zāi)難,可以說是近衛(wèi)個(gè)人性格與他的政治觀念、政治才能疊加的惡果。伊恩·克肖在其名著《命運(yùn)攸關(guān)的抉擇:1940-1941年間改變世界的10個(gè)決策》認(rèn)為,“如果他(近衛(wèi)文麿)天真到以為自己能用權(quán)力手腕來克服軍部的反對(duì),那他太低估了這些年陸海軍對(duì)日本權(quán)力體系各個(gè)層級(jí)的滲透與控制的程度。”但問題在于,近衛(wèi)文?恰恰不具備這種杰出政治家所應(yīng)具備的當(dāng)機(jī)立斷性格——且不論之前已破獲兩起針對(duì)近衛(wèi)的民族主義刺殺陰謀。近衛(wèi)文?既沒有當(dāng)首相的愿望,也沒有首相所需要的杰出政治才能,近衛(wèi)當(dāng)上首相純粹是因?yàn)樗秋L(fēng)度優(yōu)雅的貴族、政治觀念厭惡多黨制親法西斯、性格優(yōu)柔寡斷(“想取悅每個(gè)人,但無法堅(jiān)持特定的政治綱領(lǐng)”頁38)——既然首相沒有擔(dān)當(dāng),這文官政府被軍部拖著走也就順理成章,“他的個(gè)人魅力使日本民眾看不到其中潛伏的危險(xiǎn)。”
第二、三屆的近衛(wèi)內(nèi)閣延續(xù)了之前的風(fēng)格,“與其第一任期如出一轍:既優(yōu)柔寡斷又魯莽沖動(dòng)。他總是在需要當(dāng)機(jī)立斷時(shí)猶豫不決,卻又在需要謹(jǐn)慎小心時(shí)行事沖動(dòng)。”侵華泥淖擴(kuò)展為太平洋深淵并不意外。早在1940年10月4日的新聞發(fā)布會(huì)上,近衛(wèi)就威脅美國說,“假如美國有意誤解日、德、意三國的真正意圖……繼續(xù)其挑釁行徑,我們除了開戰(zhàn)別無選擇。”這種無意義的強(qiáng)硬,除了制造無謂的外交敵意,全無用處,毫無懸念,隨后的六個(gè)月里,美日關(guān)系不但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而且進(jìn)入越來越糟糕的狀態(tài)。即使經(jīng)過民間外交的努力,1941年4月18日,從美國方面?zhèn)鱽砗驼効赡艿暮孟⒅螅q猶豫豫、毫無主見的近衛(wèi)內(nèi)閣卻對(duì)此既不珍惜,也不下功夫了解它并非美國的主動(dòng)示好,傲慢與不必要的矜持將這一束希望的光芒拖滅了。直到最后,身為首相的近衛(wèi)也沒有能夠有半點(diǎn)擔(dān)當(dāng),即使他試圖阻止戰(zhàn)爭卻又無力阻止戰(zhàn)爭時(shí),依然是辭職撂挑子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直接否決東條英機(jī)的意見,作出首相應(yīng)當(dāng)作出的從中國和法屬印度支那撤軍的決定。
近衛(wèi)內(nèi)閣中最熱衷叫囂戰(zhàn)爭的陸軍大臣東條英機(jī),內(nèi)心并不認(rèn)為美日開戰(zhàn)日本會(huì)贏,但面對(duì)大眾和西方,他必須表現(xiàn)出強(qiáng)硬立場(chǎng),在他看來,這既是國家的體面,也是他自己獲取榮譽(yù)的捷徑。當(dāng)日美進(jìn)行最后的談判時(shí),日本依然在東條英機(jī)的主持下繼續(xù)備戰(zhàn),這讓美國極其惱火,談判因此更加艱難;但是,在東條英機(jī)為了避戰(zhàn)建議近衛(wèi)內(nèi)閣辭職后,卻力薦反戰(zhàn)的皇室自由派東久邇宮稔彥王繼任首相;東條英機(jī)自己應(yīng)召繼任首相后,組閣時(shí)甚至特意選擇了三位反戰(zhàn)大臣——大藏大臣賀屋興宣、海軍大臣島田繁太郎、外務(wù)大臣東鄉(xiāng)茂德,這三位位置特別重要的內(nèi)閣大臣,讓人一看就像個(gè)和平內(nèi)閣;東條內(nèi)閣上任伊始,就一輪又一輪地重新討論9月6日決議——這是經(jīng)過天皇批準(zhǔn)的所謂和談最后期限為10月15日以及和談不成即開戰(zhàn)的內(nèi)閣決議,其觀點(diǎn)也變得越來越模糊不定,而此前,這份決議是他拿來折磨近衛(wèi)的主要武器之一。而到了11月1日,就像半個(gè)多月前近衛(wèi)勸說他反戰(zhàn)一樣,東條勸說參謀總長杉山元放棄戰(zhàn)爭主張,然而,他也遭遇了與近衛(wèi)相同的結(jié)果:勸說被拒絕。
1882年,29歲的明治天皇頒布了一份日后改變?nèi)毡緡\(yùn)的文件,就是《軍人敕諭》。敕諭要求軍人無條件效忠天皇,它鋪就了直至二戰(zhàn)結(jié)束時(shí)的日本軍國主義道路,日本軍部的勢(shì)力坐大,就是從那個(gè)時(shí)候開始。在1889年的明治憲法加持下,制度意義上,日本逐漸形成了丸山真男所謂“天皇制下的無責(zé)任體系”,具體表現(xiàn)為“回避決斷主體(責(zé)任的歸屬)明確化,傾向于‘互相依賴’的曖昧行為關(guān)系的方式”(丸山真男語)。于是,軍部的強(qiáng)勢(shì)一旦成為主流,文官政府就只能跟著走,即使他們想要和平,也會(huì)在軍部制造的戰(zhàn)狼民意和少壯軍官恐怖主義刺殺氛圍中被遏制。
這種現(xiàn)象可謂貫穿了日本從1931年到1941年這十年間所有關(guān)乎國運(yùn)的重大決策過程。東條英機(jī)刻板地遵守《軍人敕諭》,他滑回到主戰(zhàn)立場(chǎng)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認(rèn)為撤軍無法告慰中國戰(zhàn)場(chǎng)上犧牲的官兵,他不肯為了避免日美開戰(zhàn)放棄與德意的聯(lián)盟是因?yàn)橛X得這樣做背信棄義;日本發(fā)動(dòng)太平洋戰(zhàn)爭前最后時(shí)刻實(shí)際上并沒有那么想要開戰(zhàn)的海軍軍令部長永野修身主戰(zhàn)的主要目的是為海軍謀取部門利益;參謀總長杉山元不肯放棄戰(zhàn)爭主張的主因居然是擔(dān)心海軍不用作戰(zhàn)卻可以獲得巨大的資源;傾向于開明的國際自由主義觀念的聯(lián)合艦隊(duì)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最初原本是反戰(zhàn)的,也被曖昧虛假的主流拖成了偷襲珍珠港事件的策劃者;認(rèn)為物資根本無法支持戰(zhàn)爭的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認(rèn)為自己無法阻止戰(zhàn)爭而成了主戰(zhàn)派;甚至連入閣條件是東條反戰(zhàn)的海軍大臣島田繁太郎,最后也被前軍令部長伏見宮博恭王親王說服,并且因?yàn)楹\姭@得巨大軍事資源而轉(zhuǎn)為同意開戰(zhàn);東條內(nèi)閣中最反戰(zhàn)的外相東鄉(xiāng)茂德最后在精疲力盡中意志消沉;而東鄉(xiāng)派往華盛頓的外交特使來?xiàng)梢黄嗾\的和平心愿僅僅成了日本軍政兩界加緊侵略備戰(zhàn)的煙幕彈……最后,當(dāng)高層決策者人人都明知日本不是美國的軍事對(duì)手時(shí),成為主流的是如此奇怪的聲音:現(xiàn)在海軍軍力比美國稍強(qiáng),開戰(zhàn)還有獲勝的可能,要開戰(zhàn)就得趁早。在這個(gè)“天皇制下的無責(zé)任體系”中,出于天皇不否決內(nèi)閣決議的慣例,即使裕仁天皇對(duì)開戰(zhàn)充滿疑惑,也不敢違例阻止——此刻,他認(rèn)為戰(zhàn)爭機(jī)器已經(jīng)啟動(dòng),而日本的軍政要員們內(nèi)心里都在等待天皇下令取消戰(zhàn)爭決議。
1941年12月8日凌晨1:30—5:30,在四個(gè)小時(shí)的空襲中,日本帝國海軍偷襲美國駐守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duì),對(duì)后者造成重創(chuàng),死傷2400人,但仿佛是個(gè)隱喻,美國的航母不在港內(nèi),躲過一劫。四年后,日本在本土重要城市遭到地毯式轟炸,還遭到兩顆原子彈轟炸,之后,無條件投降。
一場(chǎng)生靈涂炭、關(guān)乎世界命運(yùn)的戰(zhàn)爭居然就是這樣爆發(fā)的。
堀田江理在書中指出,之所以發(fā)生這樣的悲劇,是因?yàn)椤叭毡菊膬?nèi)在根本問題在整個(gè)1941年一直存在:最高領(lǐng)導(dǎo)人盡管偶爾表示反對(duì),但他們還是沒有足夠的意念、欲望或勇氣來阻擋戰(zhàn)爭洪流。”
《深淵》澄清了長期以來一些普遍的認(rèn)識(shí)誤區(qū):
一.當(dāng)年日本軍政高層的決策體制并不是獨(dú)裁制,作者給出的史料有助于清晰地說明這一點(diǎn),并且能夠與其他歷史學(xué)家的著作相互印證。
二.日本明治維新之后的軍政體制,在決策方面存在巨大缺陷,“天皇制下的無責(zé)任體系”造成了日本官僚制嚴(yán)重削蝕了政治家的能力,將軍政精英們變成了一群沒有勇氣反對(duì)錯(cuò)誤政策的期期艾艾之徒,將軍政高層集團(tuán)變成了無頭蒼蠅般的烏合之眾。
三.軍國主義綁架了所有日本人,它不僅綁架了人民,讓他們成為炮灰,還把他們基本上變成了心甘情愿的炮灰;它還綁架了血?dú)夥絼倕s無腦的少壯軍官,他們的恐怖主義導(dǎo)致了更為嚴(yán)重的軍國主義肅殺氛圍;它甚至綁架了軍政精英,使得他們變成懦夫群體,敢于反戰(zhàn)的人鳳毛麟角,即使鳳毛麟角的反戰(zhàn)者也常常因環(huán)境惡劣半途而廢。
然而,不管有多少原因?qū)е铝诉@場(chǎng)戰(zhàn)爭,最大教訓(xùn)依然是:任何一個(gè)國家,其主政者永遠(yuǎn)都是國家和平與安危的第一責(zé)任者——懦夫常常比勇士更敢于叫囂戰(zhàn)爭,因?yàn)樗麄兪菬o需負(fù)責(zé)的群氓,是勒龐所謂集體和人群中的“無名氏”,他們的叫囂只是虛假的空氣震動(dòng)。真正的勇士往往是力排眾議、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反戰(zhàn)者,他們熱愛和平,才選擇了反抗愚蠢和不負(fù)責(zé)任。對(duì)軍政精英而言,戰(zhàn)或不戰(zhàn)都不是勇氣的標(biāo)志,負(fù)責(zé)任、維護(hù)和平才是真勇敢。任何一國的軍政精英,肩負(fù)安邦守土之責(zé),本不應(yīng)當(dāng)向?yàn)鹾现姷木薮笤胍粝鹿颍瑹o論這種烏合之眾出現(xiàn)在哪里、有多大的規(guī)模——不知道絞刑架上臨刑的近衛(wèi)文?和東條英機(jī)是否想過,那些曾經(jīng)海嘯般此起彼伏的狂熱叫囂,而今安在哉?
作者=李維清
本文系《經(jīng)濟(jì)觀察報(bào)·書評(píng)》原創(chuàng)稿件